经典案例
经典案例
对方迟迟不开发票,能拒付剩下的钱吗?最高法院给了答案
东莞律师获悉
对方拖延开具票据,可以拒绝支付剩余款项吗?最高法院一个表态,让不少企业未曾想到的自我保护措施

有一桩事件,简而言之就是一起表面上的单据争议,最终导致六百五十万的执行问题被提交到了最高司法机构。瑞某特企业同某煤机企业达成了和解协议,商定在收到税务凭证之后支付剩余的六百五十万元款项。这家煤炭设备企业依照约定支付了大部分款项,但对方并未开具发票,因此这家企业拒绝支付剩余部分,对方随后申请恢复执行却遭到拒绝,最高法院最终确认了不恢复执行的裁决结果,这一判决表面看似明了,实则反映了一个企业合同管理中很容易被忽略的潜在风险点。
坦白讲,初次接触时不少机构会立刻回应“若对方拖欠款项就应采取强制措施”,然而法律并非总是遵循这种想法。最高法院这项判决强调契约本质:若和解协议系双方互负义务的双务契约,且约定一方履行作为另一方付款的必要前提,那么后履行方在先履行未完成时行使抗辩拒绝支付,并非等同于违背和解协议从而恢复诉讼程序。换言之,合同条款是否明确,直接关系到司法裁判的权限范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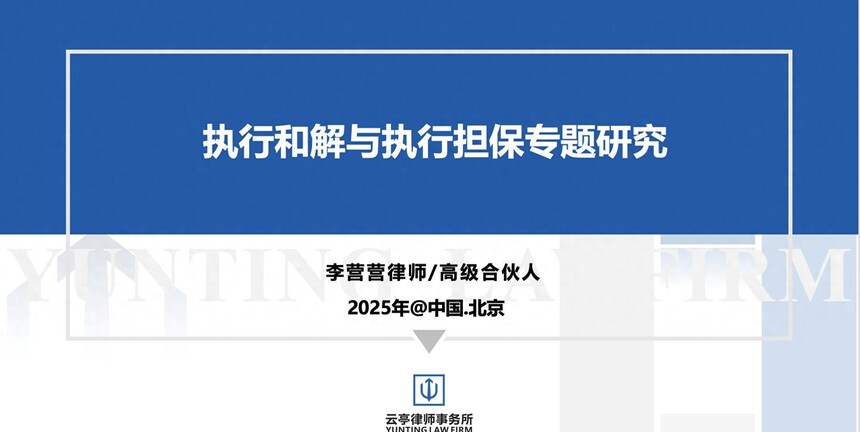
这位裁判对企业有显著作用。作为债权方,或许会认为开票只是常规流程,但一旦发票变成合同里对等的交换条件,不开发票反而可能成为有效的理由。这种情况导致许多原本期待法院支持追款的案件,最终可能因合同约定不清而败诉。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对债务人而言并非没有代价,这种权利是有时间限制的,如果对方之后修正了履行行为,或者司法机构判定抗辩理由不成立东莞律师,那么原先的抗辩优势就会丧失,债务人依然可能承担被执行的后果。
我有个朋友叫小李,他从事机械零件销售,曾经因为票据事务打了两年的官司。协议上写明“货物一到就开具票据”,但对方在收到货物后,却以票据不合要求为由不肯支付剩余货款。小李当时没有在协议里把开票当作必要条件,也没有妥善保管好物流签收、电子核销这些材料,因此在法庭审理时,法官更注重实际付款和收货的经过,最终判决让小李损失了数十万的资金周转。这件事让我明白,诸多争议往往在协议签署阶段就已埋下隐患。
实际操作中,怎样减少风险呢?合同内容需要尽可能清晰界定执行步骤和执行标准,把重要的附加责任讲明白,说明“取得发票是支付尾款的必要条件”。另外,维持履行凭证的完整性很关键,开具票据、物品交接、账目核对、邮件往来、银行凭证等环节都要有记录。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管,或者设立分期支付和交付环节,将巨额尾款存入独立账户,或通过公证、存证方式,使其成为具备法律效力的证据链。如果对方延迟履行辅助义务,行使先履行抗辩时需考虑违约程度——轻微问题不应拒绝履行核心义务,而严重违约或根本性缺失则可以拒绝支付相应款项。
从审判者的立场出发,他们会对执行恢复的申请进行四个层面的考察:协议是否已经完全履行、约定的前提条件是否尚未达成、义务人是否在依照和解协议履行,还有是否存在其他不适宜继续执行的情况。司法机关不会将异议简单视为阻碍执行的借口,同时也不会无条件地否定申请人的诉求。换言之,恪守诚信始终是司法裁决的根本依据,恣意行使抗辩理由来逃避偿还责任者,无法博取认可。
未来情形或将是:司法机构将更加重视合同双方对执行次序的商定,不过亦会将均衡理念与诚实理念视作核心,责令合同签署者明确主要条款,并妥善保存相关凭据。公司对法律风险的管控或许会从“事后清收”转变为“事先控制”,法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信息交流会更紧密,像发票开具、产品交付、款项核对这类表面上看不起眼的工作,会变成合同磋商中的核心内容。
在提出处理意见时,债务人需在协商或交易协议中明确注明票据的种类、开具期限、传输途径以及违反规定的相应责任,同时准备好能够被司法机构或仲裁组织认可的证明材料。欠债人要审慎行使先履行抗辩权,在拒绝付款前,必须确认对方是否已经完全履行了核心责任,同时要考虑抗辩的时效性和合理性,必要时需要用书面形式说明或者保存沟通凭证,以防将来被指责为恶意拖欠。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时,也可以事先明确约定争议处理方式、执行暂停条件、履行保证等事项,这样一旦产生矛盾,司法机关在审理时就能有清晰的参考标准。
说到底,这类争议的关键不在于法规有多难懂合同履行的证据,而在于合同执行中的具体环节决定了能否追回款项。通常一个附加条款、一张邮寄凭证、一封确认函件,就能左右案件结果。企业负责人或法律人员,不要小看发票问题,不要将和解作为唯一手段。要提前防范风险东莞律师事务所,确保证据材料符合法庭要求,这样维权才能更有把握。
你们或者你们关联的企业,是否遭遇过因票据、履行次序或和解条件产生的债务争议?谈谈你们应对措施,以及当时内心的想法,以便相互借鉴经验。
依据最高审判机关在编号为(2018)最高法执监119号的司法裁定;该裁定系由李营营律师在东莞组建的团队进行汇编而成
东莞律师?敬请于评论区发表高见,并对本文予以点赞及转发,以助广大读者把握法律与正义的界限。